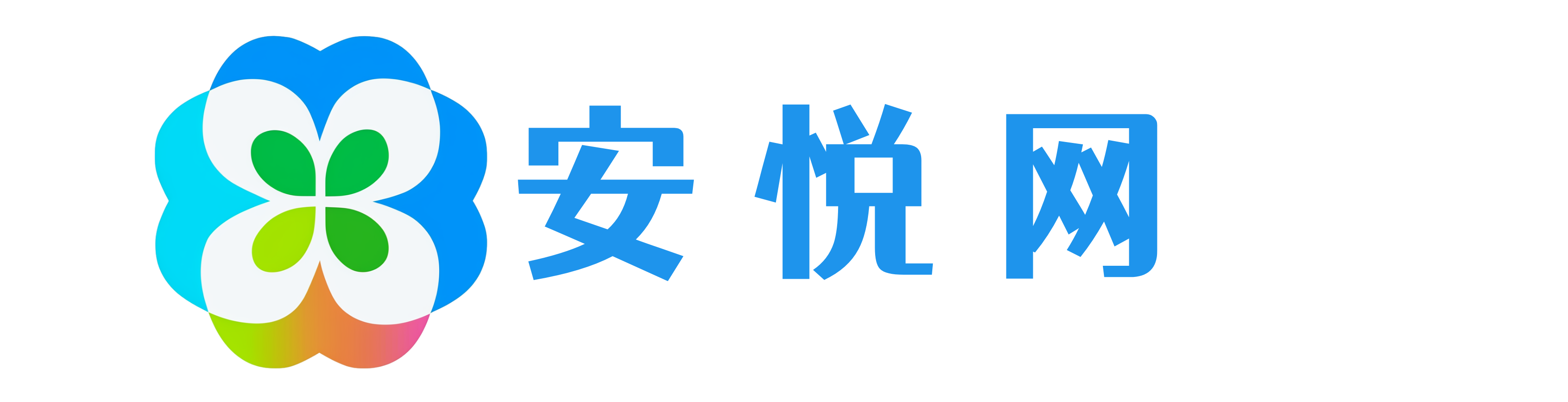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又开花了,细碎的白瓣子扑簌簌往下掉,像极了妇人纳鞋底时抖落的线头。穿蓝布衫的阿婆们总爱聚在树荫下,边搓麻绳边念叨些陈年旧话。昨儿晌午,李婶突然用顶针敲了敲搪瓷缸:"你们说,长夫子眼的女人,一百个里头能找出几个?"
三个半
这话得从镇东头的老裁缝说起。他那铺子门楣上常年悬着把铜尺,据说是祖上给宫里娘娘量衣裳传下来的。有回帮新媳妇裁嫁衣,尺子影子斜斜映在姑娘虎口上,老裁缝突然"咦"了声。后来才听说,那姑娘右手拇指根有道浅纹,弯弯绕绕像用绣花针挑出来的小月牙。
油坊张老板的闺女也有这印记。这姑娘舀麻油从不用秤,胳膊一扬就是八两准。有年腊月集上,她隔着三条街闻出掺了桐油的芝麻,惊得贩子当场跪下来磕头。但左手那道纹只到中指节就断了,老辈人说这算半道夫子眼。
井水知道
西巷王家的压水井总泛着股墨香。先前有游方先生来讨水喝,盯着井台青砖看了半晌。后来才有人发现,砖缝里嵌着些极细的纹路,排列得跟书院案头的竹简似的。打那以后,但凡谁家姑娘来打水,桶绳总要在砖上蹭三下。
最奇的是程家寡妇。她每日寅时来汲水,井绳从来不响。有回早起的货郎看见,月光下那桶水晃出来的波纹,竟显出"子曰"二字的轮廓。后来货郎发了癔症,见人就比划水纹的样子,可惜再没人见过。
灶王爷记账
腊月二十三祭灶那晚,赵家媳妇总要多备一碟芝麻糖。她家灶台后头的砖墙上有道裂痕,年头久了竟长出些枝枝蔓蔓的纹路。有年小姑子嫂子藏钱匣,发现那裂纹会自己挪位置——今日像"三"字,明日变"五"字,跟灶王爷算账似的。
最玄乎的是刘铁匠家的。他家灶眼里的火苗子会写字,有回邻居来借火种,眼睁睁看着蓝火苗扭出"七"字。铁匠婆娘不识字,倒能把《女儿经》背得一字不差,只是右手掌心总沾着洗不掉的锅灰印。
槐树底下突然传来"咔嗒"一声,李婶的顶针滚到了青石板上。众人低头去寻,却见石缝里爬着几只蚂蚁,排出的队伍恰似个歪歪扭扭的"百"字。风一吹,树影子把字盖住了半边,倒像是被谁用橡皮擦去了一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