蔡崇达的母亲是一位坚韧而朴实的闽南女性,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命运的狂风暴雨,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了希望的花。她的故事像闽南老厝门前的石板路,斑驳却坚实,每一步都刻着生命的重量。
盐碱地的玫瑰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闽南渔村,咸涩的海风裹着贫穷吹进每道墙缝。蔡崇达母亲生于这样的年代,九岁就光着脚丫踩在晒得发烫的沙滩上挖蛤蜊。家里七个孩子像一窝嗷嗷待哺的雏鸟,她作为长女,把读书机会让给弟弟时只说:"课本哪有地瓜甜。"但没人知道她深夜偷偷用木棍在沙地上练习写自己的名字,潮水一来,那些字迹就和眼泪一起被大海收走了。
扁担挑起的家
嫁给病弱的丈夫后,命运给她压上更沉的担子。凌晨四点挑着海蛎赶早市的身影,成了小镇最早的闹钟。有次台风天为保住两筐新摘的龙眼,她硬是蹚着齐腰的洪水走三里路,到家时发现龙眼筐上趴着吓得发抖的小崇达——原来孩子怕妈妈被冲走,偷偷跟了一路。她第一次打了儿子,打完抱着他哭:"你要读书,读书才能不像阿母这样活。"
缝补命运的手
蔡崇达在《命运》里写母亲"把苦嚼碎了咽下去"。最艰难时,她同时打三份工:给渔船补网,帮丧事人家哭灵,凌晨扫街。补渔网的手后来总抖,却给儿子缝出全镇最挺括的校服;哭灵赚的攒成铁皮盒里的"读书基金";扫街时背下的路名,成了儿子后来笔下故事的坐标。邻居说她像块老茶饼,越熬越出滋味。
未写完的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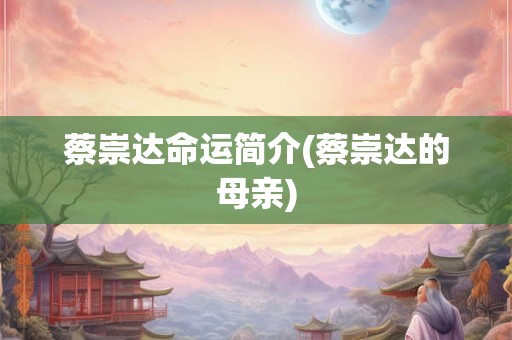
当儿子的小说获大奖时,老太太正蹲在菜市场杀鱼。记者找来时,她围裙上沾着鱼鳞说:"我囝仔是用笔在纸上种田哩。"后来她患上阿尔茨海默病,忘记煤气灶怎么关却记得给儿子纳鞋底,那些歪扭的针脚里,藏着没说完的"好好吃饭"。最后一次清醒时,她摸着蔡崇达的获奖证书喃喃:"当初沙地上写的字,到底被潮水带到好地方去了。"
这个不识几个大字的渔村女人,用最笨的办法对抗命运:像海蛎牢牢扒住礁石,任海浪拍打也不松手。而今她的影子活在《命运》的字里行间——那些粗粝的温暖,让千万读者触摸到中国母亲最原始的坚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