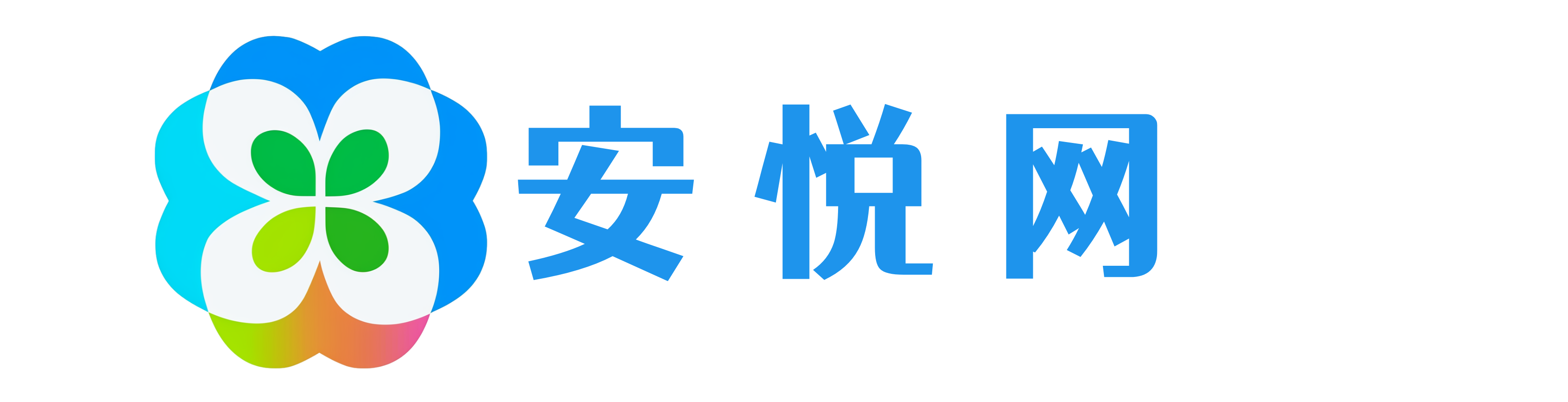夕阳的余晖洒在院子里,老槐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王奶奶坐在藤椅上,眯着眼睛看那抹渐渐暗下去的光。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磨得发亮的竹椅扶手,就像在数着那些看不见的年轮。邻居李婶送来新蒸的桂花糕,她笑着道谢却只掰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——这双曾经能包出漂亮褶子的饺子皮的手,如今连最爱的甜食都捧不住了。
食欲突然消退
人到了最后那段日子,身体会像秋后的蝉,慢慢收起所有声响。从前每顿能吃两大碗米饭的老张头,突然对着最爱的红烧肉摇头,儿子特意买的蜂王浆在抽屉里攒了三盒都没开封。不是挑食,是喉咙像被棉花堵着,连米汤都像掺了沙子般难以下咽。儿女们总以为是胃口不好,其实那副肠胃早已像老旧的灶台,再也燃不起消化食物的火苗了。
记忆开始倒带
赵爷爷把孙女的初中毕业照当成了女儿小时候,却把昨天吃的药忘得一干二净。他的记忆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,越是近处的事情越抓不住,反倒是几十年前合作社分粮的细节能说得一字不差。有天清晨他忽然穿戴整齐说要接放学的小儿子,可他那最小的孩子今年都已经四十有二。这些记忆的错位,恰似生命在悄悄整理最珍贵的行囊。
钟爱旧物

陈老太的搪瓷缸掉漆掉得看不出花样,儿女给买的保温杯她碰都不碰。临终前半个月,她突然翻出结婚时的红棉袄抱在怀里,那布料脆得稍用力就会裂开。人到最后总会本能地贴近那些带着体温的记忆,就像树老了一定要把养分送回最深的根系。儿女们不懂为什么老人突然痴迷这些破旧物件,其实那是他们在用最后的气力拥抱自己的一生。
看见"那边"的人
弥留之际的李奶奶总对着空椅子说话,她说早逝的老伴来催她了。护工吓得汗毛倒竖,学过医的孙子却悄悄拉开窗帘——阳光把晾衣架的影子投在墙上,恰似个弯腰的人形。这些亦真亦幻的对话,不过是疲惫的灵魂在现实与彼岸之间踱步。就像困极了的人眼前会浮现梦境,生命将尽时,那道生与死的门帘自然会变得透薄。
安排身后事
周老爷子突然把存折密码写在台历上,把每件毛衣该送给谁都叠好标了名字。女儿红着眼眶说他胡思乱想,老人却笑着说:"早晚用得着。"这种突如其来的清醒,像蜡烛熄灭前最后那簇明亮的火苗。他们不是突然变得豁达,而是听见了生命倒计时的滴答声,急着要把人间的牵挂都归置整齐。
窗台上的月季今年开得特别艳,王奶奶却再没力气去修剪。某个有露水的清晨,她像平时一样靠在枕头上闭目养神,只是这次呼吸渐渐变成了细弱的涟漪。床头那本翻旧的相册摊开着,最新的一张全家福上,她穿着那件褪了色的红棉袄,笑得像朵风干的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