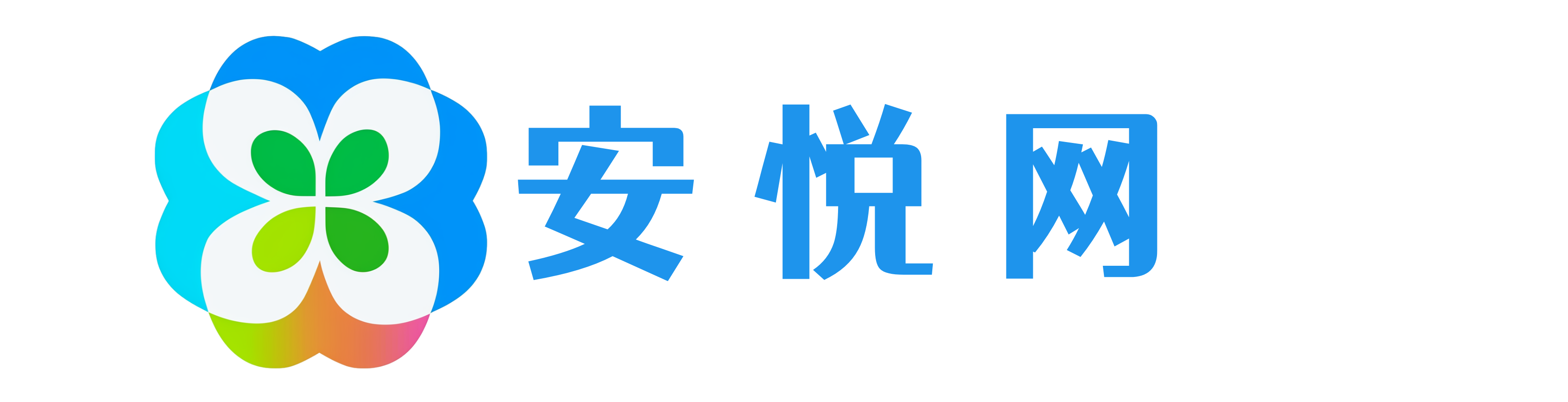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,梦里我握着把生锈的柴刀,手起刀落间,一条花斑蛇的脑袋就骨碌碌滚到了草丛里。醒来时掌心还残留着冰凉的触感,仿佛真捏过那条蛇的七寸。这梦实在蹊跷,让我一整天都忍不住琢磨其中的门道。
斩蛇的瞬间
梦里那蛇其实没招惹我。它正盘在青石板上晒太阳,鳞片泛着彩虹色的光,吐信子的动作慢得像在打哈欠。可不知怎么的,我抄起脚边的柴刀就扑了过去。刀锋卡进蛇颈时手感特别真实——先是遇到韧骨的阻滞,接着"咔"地一声脆响,蛇头飞出去的轨迹像被慢放的镜头。最怪的是,断口处竟飘出几缕白烟,带着庙里香火的味道。
血变成了藤蔓
本以为会看见血溅三尺,结果地上冒出的是一簇簇嫩绿藤芽。这些藤蔓疯长得离谱,眨眼间就缠住我的脚踝往地下拽。蛇身子也没死透,断颈处突然裂开成五瓣,像食人花似的咬住我手腕。这时候才注意到,柴刀把手上刻着歪歪扭扭的"冤"字,锈迹里还掺着几根女人的长发。
老槐树在笑
挣扎间抬头,发现场景变成了老家祠堂后院。那棵吊死过人的老槐树正在晃枝条,树皮皱褶里浮出张人脸。它每笑一声,藤蔓就收紧一分。快窒息时,断头的蛇突然用尾巴尖蘸着自己的血,在我裤腿上写了"三日"俩字。这时闹钟响了,我浑身汗湿得像从河里捞起来。
白天的蛛丝马迹
吃早饭时新闻正播某工地挖出宋代蛇形陶俑,镜头闪过陶俑脖颈处的裂痕,跟我梦里砍的位置分毫不差。中午路过菜市场,卖甲鱼的摊主突然拽住我说:"你印堂发青,最近别近水火。"更玄的是回家路上,总听见草丛里有东西跟着我爬,回头却只有被风吹动的狗尾巴草。
藏在记忆里的钥匙

直到晚上给外婆打电话,她听完沉默半晌,突然问:"你还记不记得六岁那年?"原来当时我在坟场玩,被条青蛇咬了脚踝。后来有个穿红袄的疯女人冲过来,徒手扯断了蛇头。外婆压低声音说:"那女人第二天就投井了,井口...正好对着咱家厨房窗子。"
现在书桌上的台灯总莫名其妙闪烁,每次灯光暗下去,都能看见窗玻璃上浮着个模糊的红影子。我盯着那把根本不存在的柴刀,终于明白"三日"是什么意思——明天就是疯女人的忌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