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将至,细雨纷纷打湿了青石板路,空气中飘散着纸钱燃烧后的淡淡焦香。老街坊们提着竹篮穿梭在巷弄间,篮中装着新折的柳枝和还冒着热气的青团。李奶奶蹲在门槛边叠着金元宝,忽然抬头问路过的张婶:"听说老王家上个月走了老爷子,这新坟是不是得赶在清明前去祭扫啊?"张婶手里的艾草顿了顿,几片青叶飘落在潮湿的苔藓上。
需提前祭扫
在江南水乡的习俗里,新坟就像刚出生的婴儿需要特别照料。老人们常说"新坟不过社",意思是亲人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,最好选在春社日(立春后第五个戊日)前完成祭扫。这就像给远行的旅人提前备好干粮,让逝者在陌生的世界里能早些收到亲人的牵挂。
去年隔壁单元陈叔走的时候,他儿子特意从深圳赶回来,在清明前十天就带着新鲜樱桃和薄荷糕上了山。当时我不太理解,直到看见陈婶红肿着眼睛解释:"新去的魂灵认不得路,得早点给他们引方向。"她说话时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墓碑上新刻的描金字,晨露把她的布鞋浸成了深蓝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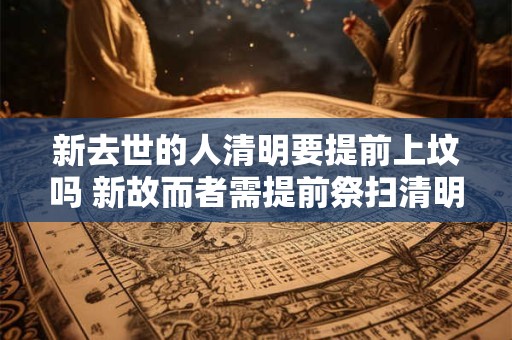
提前十日为宜
具体要提前多少天,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讲究。江浙一带多选清明前十日,就像给重要约会留出缓冲期;而闽南地区则讲究"头年不过午",要在正午前完成祭扫。这让我想起外婆生前总说:"太阳最旺的时候,活人死人都能接着热气。"
表姐嫁到皖南那年,正赶上婆家老太爷过世。她记得清明前整半个月,全村的新坟前都飘起了白幡。女人们用竹筒装新酿的米酒,男人们扛着铁锹修整坟头草,孩子们把刚摘的野花摆成圆圈。那种热闹不像哀悼,倒像在给远行的亲人办欢送会。
心意重于形式
其实提前多久并非绝对,关键是要让心意走在时间前面。邻居赵老师是退休的历史教授,他父亲去年冬至离世。今年清明他只在坟前放了本《楚辞》,书页里夹着父子俩最后在病房里下的那盘棋的棋谱。"老爷子等不及看今年的新茶了,"他说话时正把雨水从眼镜上抹去,"但精神上的祭扫,我们天天都在进行。"
巷口卖海棠糕的阿香嫂说得更直白:"活着时候多端碗热汤,比走后烧千万张纸钱都强。"她每天清早仍会留出第一炉最完美的糕,放在丈夫遗像前——虽然他已经走了三年。
雨停了,李奶奶终于叠完最后一串金元宝。她起身时膝盖发出轻微的响声,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。"明天就让我家小子开车上山,"她把元宝仔细收进蓝布包袱,"新去的路上冷,得让老头子早点收到冬衣。"远处不知谁家的小孩在唱童谣,声音穿过湿漉漉的樟树叶,惊飞了几只正在啄食祭品残渣的麻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