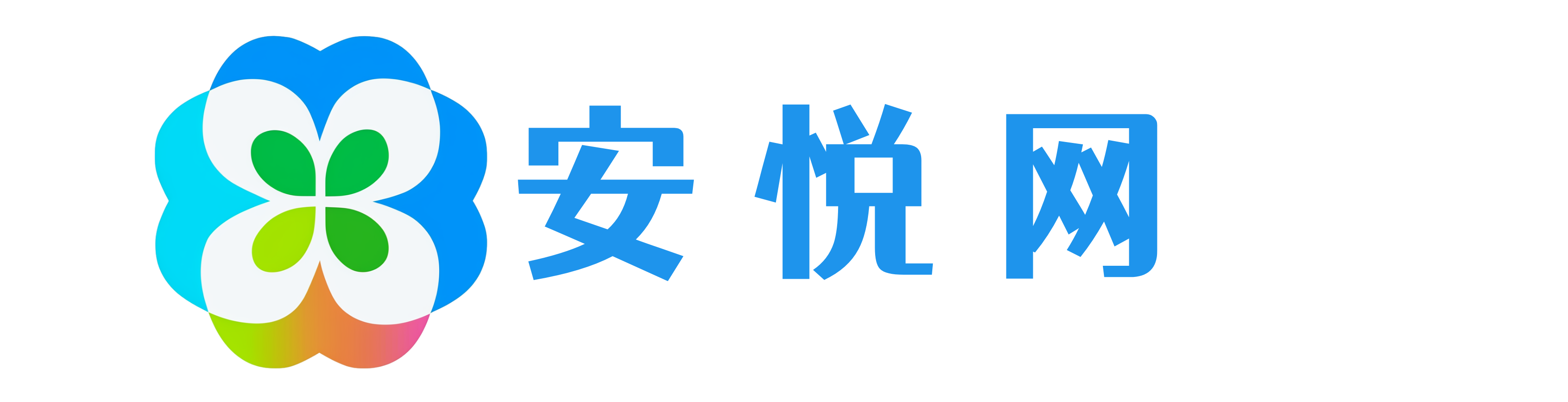昨夜,我又梦见了那个熟悉的小院——斑驳的土墙上爬着牵牛花,灶台边飘着葱花烙饼的香气,二婶系着蓝布围裙在井台边打水,木桶磕在青石上"咚"地一声响。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做这样的梦了,每次醒来枕巾都洇着湿意,仿佛故乡的晨露透过梦境渗进了城市的高楼。
老屋的咳嗽声
梦里总先听见那扇榆木大门"吱呀呀"的动静,像老人起床时的咳嗽。门槛上被雨水泡出的凹坑还在原处,我六岁那年摔跤磕掉的木屑依旧缺着一角。堂屋八仙桌上摆着搪瓷缸,祖父的烟袋锅斜靠在缸沿,顺着缸身淌出琥珀色的泪痕。最神奇的是连霉味都那么真切——梅雨季时衣柜散发出的陈旧气息,混合着米缸里新稻谷的清香,在梦里织成一张温暖的网。
井台边的闲话
二婶打水的姿势二十年没变,弓着背把辘轳摇得哗啦啦响。她脚边总围着几只芦花鸡,抢着啄桶沿滴落的水珠。梦里能清晰听见她和隔壁王婆的对话:"张家闺女在城里买房啦""后山李家的枇杷今年甜得很"。这些家长里短飘在晨雾里,比任何闹钟都让人清醒地意识到:这是故乡的声音。有次梦里我还看见自己蹲在井沿剥毛豆,指甲缝里嵌着青绿的豆汁。
消失的晒谷场

最揪心的是梦见晒谷场变成了停车场。金黄的稻谷本该在秋阳下铺成地毯,现在却停着几辆陌生的轿车。水泥缝里钻出的车前草让我稍感安慰——至少土地还记得从前的模样。场边那棵歪脖子枣树还在,我踮脚去够最高处的枣子时,树干上刻着的"小燕到此一游"依然清晰可辨。梦里摸着那些稚嫩的刀痕,突然就哭醒了。
灶王爷的微笑
厨房永远是梦里最鲜活的地方。土灶里柴火噼啪作响,铁锅边沿粘着半片焦黄的锅巴。母亲掀开蒸笼时,白雾裹着红薯甜香扑面而来,瞬间模糊了贴在灶台上的年画。关公的红脸被水汽晕染开,倒像是冲着偷吃的我在笑。有次梦见自己够不着碗柜,急得直跺脚,醒来发现膝盖磕在了床头柜上。
这些年故乡在梦里越来越清晰。昨夜的梦里甚至闻到了油菜花田的土腥味,看见露珠在蛛网上折射出七色光。或许正如母亲说的:"人走得再远,魂儿总在老家转悠。"每次从这样的梦中醒来,我都会打开窗户深呼吸,仿佛这样就能把故乡的空气吸进肺里,存到下一个梦境降临的时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