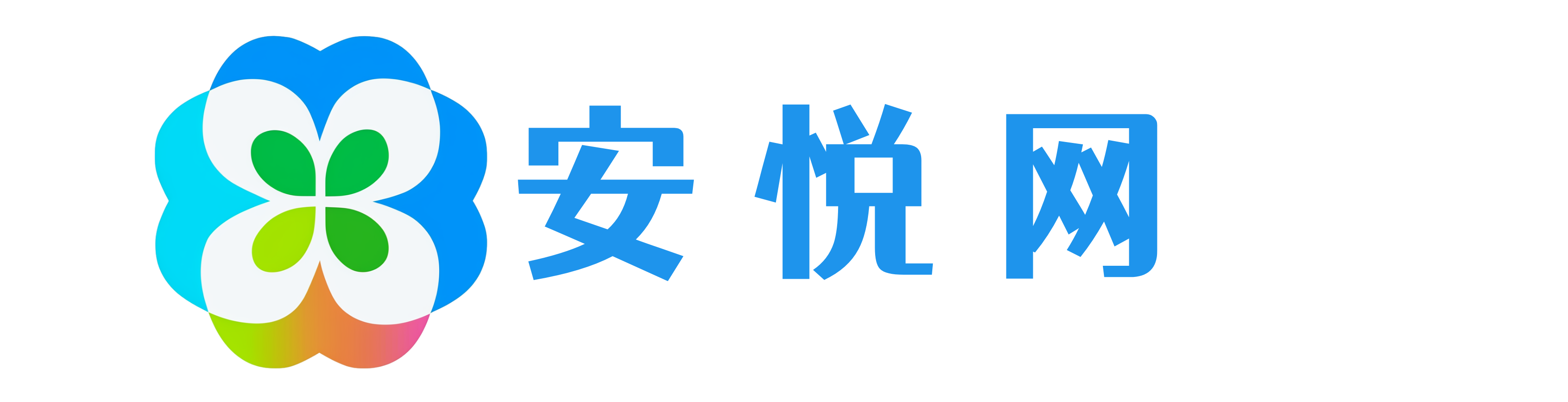午夜的血与影:一场梦里的旁观者
凌晨三点,我从床上猛然坐起,额头沁出冰凉的汗珠。窗外飘着细雨,雨滴在空调外机上敲出细碎的声响。梦里的画面清晰得可怕——两个模糊的身影在昏暗的巷子里扭打,拳头砸在肉体上的闷响,粗重的喘息混合着骂声。我就像被钉在原地般站在三米外,手里还攥着半根融化的冰淇淋。
旁观者的枷锁
梦里最奇怪的是我的双手。它们不断重复着掏手机的动作,可那台亮着拨号界面的手机总在接触到耳畔的瞬间消失。右脚下意识往前迈了半步又缩回,鞋底蹭着粗糙的地面发出"沙"的声响。打架的两人始终没有正脸,只有那个穿红背心的后颈上,一道新月形的疤随肌肉起伏时隐时现。
冰凉的黏腻感
直到穿蓝衣服的人抄起锈迹斑斑的铁管,我才发现握冰淇淋的手指已经发麻。奶油顺着指缝往下淌,在手肘处凝成浅黄色的痂。巷口突然传来野猫的嚎叫,铁管挥下的弧度突然变成慢动作,我在梦里清清楚楚看见几颗带血的牙齿飞向自己脚边。
凝固的时间

整个梦境没有对话,只有此起彼伏的呻吟。当红衣人的血漫到我鞋尖时,天花板上突然传来楼上住户冲马桶的声音。这声轰鸣成了闹钟的前奏,我惊醒时还保持着梦中僵立的姿势,双腿肌肉紧绷得发酸。
现实的余温
晨光透过纱帘漏进来,我把手掌摊在眼前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的奶油。厨房里电水壶呜呜作响,楼下的早市传来熟悉的吆喝声。但那个穿红背心者脖颈上的月牙疤,却像烙在视网膜上似的挥之不去。
直到现在泡咖啡时,我仍在想那半步距离意味着什么。是人性本能的怯懦,还是某种微妙的自我保护?梦里的我和现实中每天在地铁让座、帮邻居拎菜的自己判若两人。也许每个普通人心里都藏着这样一条昏暗的后巷,当暴力突然降临时,才发现连摸手机这个动作都需要莫大的勇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