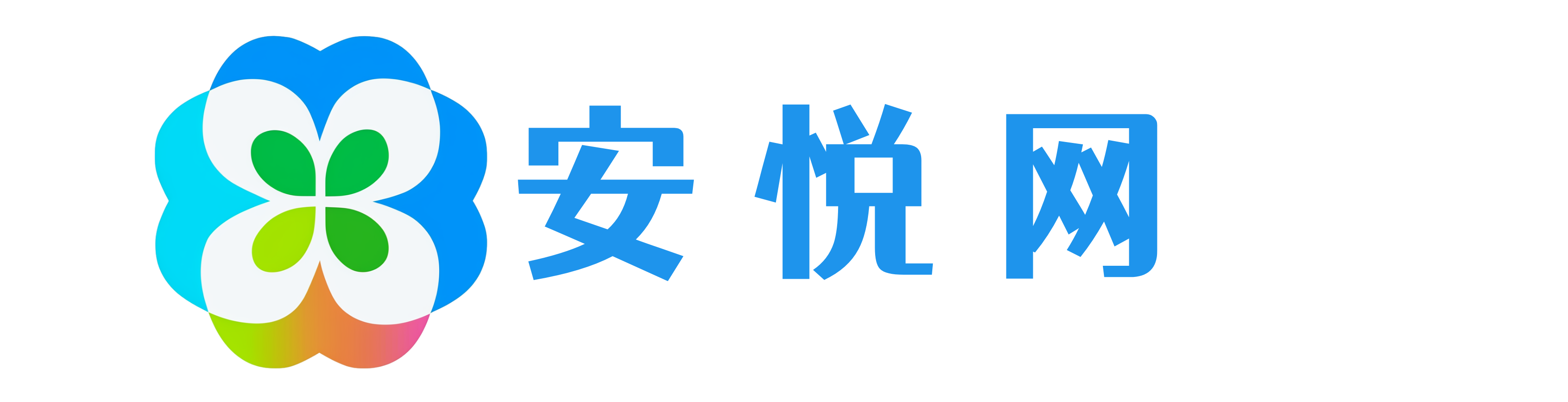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,风扇在床头吱呀转动,李梅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半梦半醒间,她突然站在贴满喜字的酒楼里,身上穿着十年前相亲时的碎花裙,对面坐着个戴金丝眼镜的陌生男人,他推过来一碟桂花糕,笑着说:"阿姨介绍我们认识的"——她猛地坐起身,发现丈夫正打着呼噜,睡衣后背湿了一片汗渍。
梦境从何而来
李梅轻手轻脚走到阳台,夜风带着楼下栀子花的味道。她想起白天买菜时撞见初恋男友,对方牵着孩子匆匆走过;想起昨天闺蜜炫耀新交的年轻男友;想起丈夫最近总抱怨公司裁员。这些碎片像打翻的针线筐,在梦里织成了荒诞的画面。其实哪有什么深意,不过是生活压力在睡梦中的投射。
婚姻里的痒
结婚十二年,她和丈夫早过了蜜月期。现在两人像合租室友,他看球赛她追剧,偶尔为谁晾衣服吵几句。梦里那个戴眼镜的男人,或许代表着她对新鲜感的渴望。就像衣柜里那件舍不得扔的旧旗袍,明知穿不上,但摸着光滑的料子就会想起二十岁的夏天。
道德不必焦虑
第二天洗碗时,李梅还被这个梦臊得脸红。其实完全没必要,人脑每天产生上万个念头,梦里出现一百个帅哥也正常。她想起表姐去年梦见变成奥特曼打怪兽,难道真要买身皮套去拯救地球?梦境就像心灵的天气预报,阴晴雨雪都是自然现象。
老夫老妻的甜
周末丈夫突然说:"单位发了电影券,要不要看那部爱情片?"影院空调很足,他像年轻时那样把外套披在她肩上。黑暗中李梅闻到熟悉的味,突然发现丈夫的手腕和梦里那个男人一样,有颗褐色的小痣。原来所谓"理想型",早就在柴米油盐里长成了最妥帖的模样。
日子照常过

现在李梅偶尔还会做奇怪的梦,有时梦见自己会飞,有时梦见中学教室。她学会了把这些当成生活的小调剂,就像炒菜时意外多撒了把辣椒,呛是呛了点,但饭总要继续吃。昨晚丈夫说梦话还在嘟囔"方案明天交",她笑着给他掖了掖被角,月光从窗帘缝漏进来,照在结婚照泛黄的相框上。